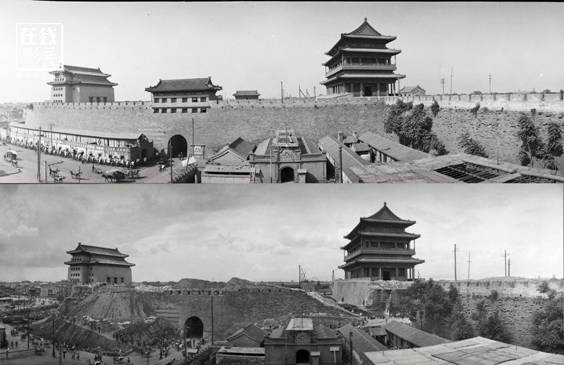然而中国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呢?尽管有积极的改革的举措。但我觉得已经失去了大方向。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就是要过河。而改革的过程是需要摸索的,也就是摸着石头。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之后的改革和发展就是在极其明确的方向下取得的。现在方向是没有,更不要说积极的改革措施了。现在的很多政策与其说是改革倒不如说是救火。我们的领导班子都是救火队,着火的地方越来越多。当然还有很多以改革名义出台的改革都是对具体利益的追求。尤其是表现在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层面,捞一把利益,各方就出现了利益导向的政策,美其名曰改革。
近年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现在越来越激进。与此同时官方在改革路线的表态上长期处于守势,只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能做什么。没有一种共同的声音。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大的方面,无论是改革的方面和正式的角度,改革是不是出现了倒退?举一个例子,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路线,并明确地表明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要保证100年不变。《人民日报》当时发表了以后很振奋人心。可是近年来虽然左派力量的崛起,我们简单地把中国社会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起来。批评市场经济,少数一些人甚至是怀念贫穷社会主义的实践。而在一些地方,很多领导都在提这个观点。
实践层面,随着国有企业的大扩张,市场空间快速地被挤压,问题是如何确立改革的方向,这是对中国改革者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我想从一个历史的宏观的角度,我们或许能够对方向性的问题看的更加清楚一些。所以我想把当代中国的改革和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建设结合起来。当代改革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建设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回答几个重大的问题,包括我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如何建立国家?我们已经走到了哪一步。现在的问题在哪儿?
所以我想从辛亥革命开始讲。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传统的皇权体制,确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是中国探索一个新型国家的开始。如果不用考虑到政治上的正确问题,我想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这一探索的组成部分。到现在为止这个过程还没有终结,这不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不一样的国家,我们要明确今后国家建设的方面就必须具有这种历史观。
这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觉得要提出来,就是要搞清楚国家建设的两个功能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国家建设包括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第二个是我们能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第一个问题是规范性的问题,我们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施政的问题,我们实际上能够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规范的问题很重要,规范性目标的提出,往往是人民碰到了一系列的国家的形势,所以要建立一个人民理想中的国家。不过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国家,人们提出很多的理想,但能够受实际的影响并不多。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更重要。我们能够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我们理想中的国家必须要拥有建设一个这样的国家的资源。我们不能空想和幻想。我们可以从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三民主义是近代来中国政治精英提出的其中一个国家建设蓝图。尽管在孙中山之前也有改革者提出了国家建设蓝图,但都没有像三民主义那样全面和系统。今天由于很多的政治原因我们不再提三民主义的概念了。可是三民主义的很多的内容我们是接受的。
三民主义也包括了国家建设的手段和方法,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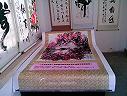
!["宇宙摇篮"会长李昌中出席钓鱼台大会[陈戈]](/UploadFiles/2013102033262043.jpg)
![“宇宙摇篮”会长李昌中简介(三)[记者:陈戈]](/UploadFiles/20131003705435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