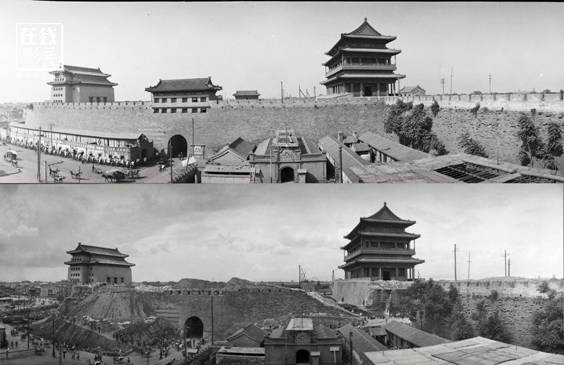胡才春(1964年——)知名作家、画家,北京总装教授)
取“虎”(之一)
“你的猫为什么画得这么好,因为我以前是画老虎的,取法于上”。(报摘)有一天我勇敢地画了一只老虎,很喜欢,置于家中,用于提神和避邪,朋友们过来都想要,我不给,一日,某报社张女士来玩,他看见这只下山虎,双眼充满了灵光,她说要,我说给您重画一幅,下次来拿,她又说,“我属虎,这又是一只受伤的‘老虎’,你看,那脑部颜色偏红,这正是我目前的处境,受了伤(得知她前不久离异)依然威猛,重整旗鼓,我现在就要拿走”,就这样,她取走了“老虎”,一个月过去了,我问她 “给老虎喂东西吃了没有”,她说伤好了,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时我看见邻家的猫发呆,呵,我的“老虎”。
害鼠(之二)
记得在一“师范”任教时,住一楼,屋旁有一小溪,常能听到师生洗衣时的欢歌笑语。老鼠喜欢把我家的家具加工成它的透雕“梅花”作品,牙齿长了,总得磨平,不过有一天,它们竟把我的国画《素梅开遍最高嵩》变成它的《嚼碎白梅落雪花》,对这种“烂尾”改造,我表示愤怒,终于在卫生间墙角发现了一个黑洞,于是找了一瓶“一得阁”墨汁倒了进去,只听见里面在说“今天,天黑得真快,谁又尿尿了,睡吧。”接着我又抓了一把辣椒粉放进洞里,为的是给点刺激性的颜色看看,结果它们都在咳嗽,声音一浪高过一浪。随后我又倒了一斤菜油进去,让它们粘得难受,好从此不再光临,最后倒上一壶开水,给它们洗个热水澡。
第二天,王老师说她昨天洗衣服时,看见一个黑得不能再黑且闪着金光的小东西在小溪里拼命地洗澡,它还说“就会用我们的胡须做成‘鼠须笔’,真是的。”
握手(之三)
清华附中的日子,清淡而有奇,那闪亮的情节常在我脑海中跳跃,有一回教师和领导去各班示以新年的问候,我习惯性地走在后面,一进某班教室,那位上课爱搬弄桌子、拆拆螺丝的小个同学(曾被我认为是未来‘土木工程系’的学子)像发现新星一样向我扑来,握着我的手,上下摆动,节奏加快、跳起来,我虽不高,但还是弯着腰陪他跳,只见一宣传委员拿着相机,一闪一闪,大伙都笑了起来,过节嘛,有气氛。可是在其它场所,如我去食堂,学校放学,只要他看见我就会握手跳跃,兴许其他师生会认为我们有病,但我真的一直想“病”下去,“病”到我的学子长成参天大树,只有“病”的老师,没有“病”的学生。
花季(之四)
总装大学的生活,别有一番风采,一学员说:“我真羡慕你母亲,有这么一位优秀的儿子。”“那我就叫您一声妈妈吧”,我说。不久,这学员把我拖到“女侧”急急忙忙地拿出一张票,“教室人多,你自己去领‘哈根达斯’月饼吧”,天啦,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有味道的月饼,又有一位学员,“老师,我这几天画了三十多张画,每当画画特别精神”从此,大伙把画挂在教室时,我就看见她的画像挂历一样的特别厚重,横向评了大伙的,还要纵向欣赏她的。虽然他们大都是六十开外的大校,将军,但这六十多位学员学习特别认真,特有精神,我只能尽情地展示技艺,以争得年轻的席位。兰花课中,我在黑板上方画了几组花朵,我叫了三位同学上台用色粉笔临摹,结果上来了一大片,她们先抢七彩粉笔,后挤黑板间隙,大显伸手,赤紫橙黄,偏偏那次没带相机,不然《花季》摄影作品一定会获奖,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可这难忘的一幕虽然不能从镜头中走出,但它一定能从钢笔中走出,一定能从画笔中走出,一定能从旋律中走出,一定能从记忆中走出。花季,永远是一种激情、一种爱美之心,一种全新的姿态。
飞跑(之五)
上高中时,我每次晚上去县文化馆参加美术培训时都要经过围墙边的一条小路,小路上堆满了垃圾,蛤蟆跳来跳去,加之又没有路灯和手电筒,我想若是踩着本来就黑晚上更黑的蛤蟆,那有三个过程:彼此怪叫、汾泌毒素出一身冷汗、死亡晕倒,于是决定飞奔而去,越快越好,从此我更加勤奋,离开了郊区,考上了艺术学府。毕业后我分在一个师范学校任教,学校建在一个满是坟地的山上,蛇很多,有没有恐高症上四楼的小花蛇,有欣赏洗衣妇的水蛇,更有串亲戚的无名蛇,每次看完晚自习回宿舍要经过一条林荫道,枝繁叶茂,深度近视,路灯己无多大作用,我想若我踩着蛇,也有三种情况:踩着尾巴,它反咬我一口,我晕过去;踩着腹部,它先咬我一口,然后用尾巴抚摸我一下,我死去活来;踩着头,它用尾巴拥抱我,我受宠若惊,免不了要拥抱它。于是,还是选择了飞跑。从此,我执著追寻,来到了清华任教。在北京,人才济济,节奏又快,我在静思,我在发明,作为人比“飞跑”更快的词语。
投稿(之六)
91年,是我最忙的一年,忙得我没有时间去痛苦或做没有意义的事。中文深造,教研组的工作,孩子出生,班主任工作,兴趣小组辅导,教学工作,家务事等等,可对一个渴望创作的我来说,还是学会了“挤时间”,如朋友来玩,就确定一个话题,最后我又把它写成文章;如我烧菜,看书肯定不合适,就用“耳朵”来获取知识,并一边跳舞一边做菜;如上街买菜,在途中构思,这当然危险,有一次路过一个圆盘,结果又走了回来;如带孩子时,一只手抱着他,一只手写作,等他大一些了就给他讲故事,通常我讲四个,他讲一个,有时双双发表。就这样,半年中,我投稿五百余篇(幅)次,时而厚积薄发,时而泥牛入海,积小成多、聚溪成河,集河成海,至今己在《人民日报》、《美术》杂志等报刊发表千余篇(幅),每次收到样刊就像收到“入学通知”那样兴奋,最后把“作品”送进了中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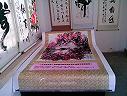
!["宇宙摇篮"会长李昌中出席钓鱼台大会[陈戈]](/UploadFiles/2013102033262043.jpg)
![“宇宙摇篮”会长李昌中简介(三)[记者:陈戈]](/UploadFiles/20131003705435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