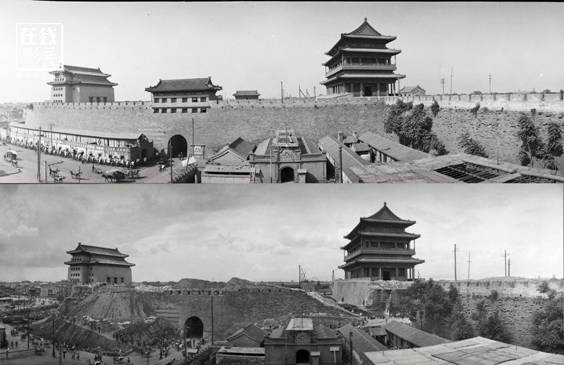代际权力的争夺与捍卫
不管成长过程中曾经遇到什么,每一代人都会有掌握社会话语权的一天,当他们老去时,也会对话语权尽力捍卫。
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莫不如此。很多人都曾说父母年纪越长,便越固执,其实这就是对自身权威受到威胁的感知,对父母权力的一种捍卫。
喻国明曾说,“任何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话语周期”,“在这个周期中,话语表达的第一个高峰是在20多岁的时候,因为年轻人对现有秩序不认同,他们的言行代表了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反叛和挑战;第二个高峰则是到了四五十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已经掌握了社会话语权,他们的观点代表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从这一点来说,两代人的冲突在所难免,亦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在中国,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甚至更烈,这是因为成长环境的巨大差异。老人们因曾经的动荡和狂热而固执,年轻人则相对理性和善。
时寒冰曾说过一句看似极端、但实际上极有道理的话:“如果从道德的沦丧和人性良知的泯灭两方面来看,从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经历的悲剧和由此造成的灾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这种灾难的影响,始终延续。
曾有年轻人这样质疑自己的上一代:当文革使中国陷入巨大混乱时,你们除了打老师、喊口号、贴大字报、搞批斗,还做了什么?如今的各种社会问题,不也正是掌握着话语权的你们造成的吗?造假的企业家们不是80后,脑满肠肥尸位素餐的官员不是80后,可你们为什么最喜欢慨叹“如今的孩子不像话”?
更让许多年轻人感到痛苦的是:他们恰恰是被上一代人教育出来的,在成长过程中,他们无时无刻都在感受着已逝去时代的遗毒。
比如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冲突,就是两代人之间的一道鸿沟。1949年以来,功利主义教育始终延续,具象呈现为人文教育的匮乏、美学教育的缺失。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常听父母说这样的话:“别看这些没用的书,好好学习”——书被强行分为“有用”与“无用”,本身就是一种功利化思维。至于学钢琴、学奥数,都是为了考试加分,而非陶冶情操或锻炼逻辑思维。功利主义本身也导致了对“前途”二字的固化,按部就班、走前人的路成了主流。如公务员热,一方面有待遇、稳定等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客观体现了思维的局限。所谓的“为理想献身”、“为艺术寂寞”,在这个时代甚至成了“傻”的代名词。无论从政从商、学术艺术,上一代人所追求的都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和好处,并力图将这种思维灌输给下一代。
与此同时,道德上的缺陷也被无限放大,并进而“传染”给下一代。历次运动中的混乱,直接导致了道德缺失,如互相举报、打砸抢,都体现了人性中极恶的一面。这种道德上的滑坡,以及公德教育的缺失,也呈现于今日社会,大到食品造假,小到闯红灯、随地吐痰,莫不如是。而“闯红灯可以节省时间”之类的理论,竟然也成了上一代人的“生活经验”。
最可怕的,也许还是“非黑即白”二元思维的流毒。从那个从思想到言行、着装都务求统一的年代里走来,上一代人最忌讳的就是“不一样”。在他们眼中,孩子若是跟别人不一样,那就是不可饶恕的大罪过。所以,在年轻人的成长过程中,常见粗暴的干涉。他们已经习惯被国家安排,所以也热衷安排孩子的生活。而因为对自身权威的维护,不尊重孩子的上一代人,往往最爱强调子女对自己的尊重。公交车上的暴力,同样是源于这种“求尊重”。
我甚至悲观地认为,随着“运动的一代”纷纷老去,公交车上的暴力老人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曾经砸毁一切,那也许是他们一辈子中最荣耀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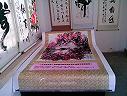
!["宇宙摇篮"会长李昌中出席钓鱼台大会[陈戈]](/UploadFiles/2013102033262043.jpg)
![“宇宙摇篮”会长李昌中简介(三)[记者:陈戈]](/UploadFiles/20131003705435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