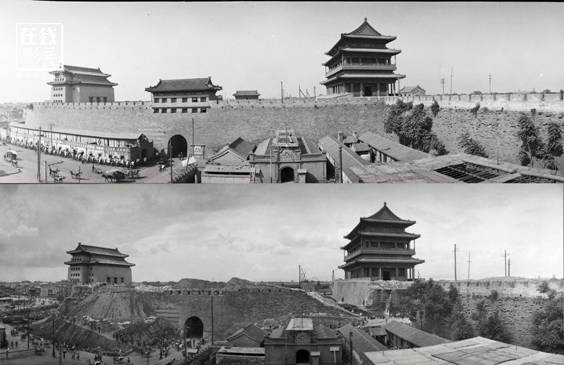岳 靓 (山东沂南)
秋末,走进承载着太多底蕴的常山庄。因了常山庄已成为影视基地,有剧组正拍摄抗日影片,未等进庄便听到阵阵炮火声,看见硝烟弥漫在深秋的田野上。我一向喜欢安宁淡泊的环境,然而走在这静谧古老的村庄,眼前却不由得浮现那段可悲可叹又可歌可泣的,战火纷飞的岁月。
站在中国红嫂革命纪念馆前,听着她们伟大又似家常的事迹,心里除了敬重,竟还掺杂了丝丝的酸楚,这些平凡而又伟大的红嫂们,值风华正茂时,既不能如我们一样静享天伦,亦不能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甚至,还要饱受惊吓与伤残病痛、生离死别。尽管生活艰难困苦,她们依然默默地承受,并用最纯净的情怀和质朴的母爱,在战火中静静的谱写着她们美好的追求和超越尘俗的美丽。
每一个红嫂的经历和故事都让人震撼,她们不仅勇敢无畏,更是充满智慧与博爱,最重要的是她们的事迹在当时竟是那么普遍,竟连乳汁救伤员的故事,也不止一例,这是怎样的大爱大勇与大智啊!
抬起含泪的双眼,正午的阳光拂过漫山果儿,金的是柿子吗?还是沂蒙母亲博爱的光环?红的是山楂吗?还是红嫂们对祖国的赤子之心?
金红的阳光温暖的铺渡上红嫂的塑像,红嫂的脸,在金色的阳光中,带着母亲特有的安详与慈爱,无声的微笑着……古人说,忘战必危,我虽厌倦说教的语言,可是,在这样安宁祥和的日子里,在这些大爱无声的红嫂们面前,我要说,一个饱受战乱的民族必须要牢记这句话。
几盘历经岁月剥蚀,默默站立在村子角落的石碾,始终温情地守护着这座村庄,进村映入眼帘的这几盘石碾,轻易地将人带进三十年代古朴的风韵里。曾经和石碾相依相随老槐树,许是因了它有某些象征意味而留了下来。穿越程程迢迢,烟火红尘,依然安之若泰,凝望他们一起慢慢衰老的容颜,一种心酸的柔情弥漫在心间。
轻轻推动石碾,想让老槐树再听听石碾吱吱呀呀的诉说:诉说那春耕时暮归老牛“哞哞”的叫,盛夏知了欢快的笑,仲秋丰收的悦,隆冬时节的冷以及红嫂们英勇无畏的故事......而今,石碾静静地站立,岁月已随着那棵老槐树的轮回渐渐远去,看着三三两两农作归来的乡民,还有在石碾下觅食的母鸡,还有升腾在院落里的袅袅炊烟,还有……还有……衰老的,不只是时间,还有战争前那些粗茶淡饭的日子,世外桃园一般的安宁。
一条条简约质朴的小巷,蜿蜒伸向远山的怀抱,巷子两边稀落着青石垒蕺的低矮的茅屋,更有几扇山枣树枝扎结成的篱笆门,隔着院子里外,把阳光切割成钻石,星星点点,镶满豆架菜地、石桌农具,还有几枝解落叶子,坠挂着金色果实的柿子树枝裸出墙外,亲切了这一张纤尘不染的画面,悄悄迷住了我的脚步……
沿着这条幽深的小巷,拾级踏上似薄又似厚的石径,轻渡在这方流年光影里,前方一抹阳光从巷尾溜进来,拂起一地斑驳的温暖,透过一扇半掩的篱笆门,我看到农舍里瘦箾的镰刀幸福的斜倚在盛满粮食的竹篓上。屋檐下挂着的一串串辣椒,在秋阳的痴痴目光里,羞红了娇俏的容颜。一棵苍劲的老柿树,伸张着干瘦的枝桠与蓝天闲聊,慈祥的把枝头泛金的果实递向白云。流光静好,安闲若诗,仄仄的小巷深处,你是否看到一位烁烁如山花的姑娘浴着阳光,轻快地跑来?此刻,我无措地站在寒山下的石径上,手里拿着相机,还是深憾自己无法让这浓郁的田园的诗意,凝固,凝固成永恒。
在这样一个暮秋的午后,邂逅这一地金色的浪漫,让我一种似梦似幻的错觉,无从想象,刚从原生态的中国古村出来,未曾回归现实,又闯入这片极具异国风情的浪漫里。
一树金黄的小扇,一地的飘飞的蝴蝶,让同来的拍客们连连惊呼,这些看似寂寥的金色蝴蝶们,善解人意的摆着娇媚的POS,合着快门轻快的追逐嬉闹,翩翩起舞。一阵风起,落叶漫天飞舞,许是因了它的从容淡定,飘落的姿态美若仙子,这芸芸众叶如同芸芸众生,带着淡淡的禅意,微醉的浪漫,红尘十里,历经三季的人世尘缘,曾青葱绚烂,曾扰攘忙碌,曾笑语嫣然,曾风沁雨润,在这个暮秋的午后,都随着倾城的斜阳,逐梦天涯……
一场诗意的邂逅,不经意间醉了北山,刚毅的脸膛,潮起层层酡红,抬眼间,谁又在醉意朦胧中把绀青、铜红、藤黄以及难以计数的浓绿,一股脑儿的抹满这连绵的北山?更兼阑珊处,时隐时现的竹篱茅舍和点点或白或黑的羊群,怎不让人陶醉在酒至微醺的意境里。挽一绺秋风,奏一曲洞箫,披一袭斜阳,笼一袖香寒,将诗的断章,画的点染、乐的飘逸,写进刚劲的山脊。
融进濛濛的山色,轻触嶙峋俊秀、感念风雨沧桑、钟情悠然无尘,满目空灵,微醺的北山,醉了我的眼,醉了我的心……
编辑:樊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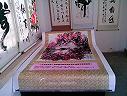
!["宇宙摇篮"会长李昌中出席钓鱼台大会[陈戈]](/UploadFiles/2013102033262043.jpg)
![“宇宙摇篮”会长李昌中简介(三)[记者:陈戈]](/UploadFiles/201310037054350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