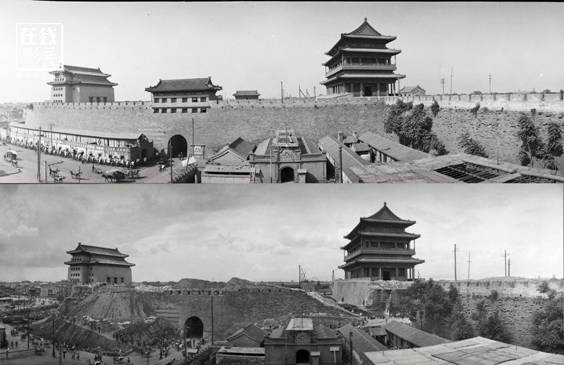一位乡村彝族教师的少年情怀,一段阳光的心路历程,一个个平凡如狗尾巴草一样的小人物的故事,在黔西北这块厚重的土地上,在黑颈鹤的故乡,在神奇乌蒙广袤的天空下,凝成一朵......
--自杨光早的文学作品集《六角雪花》
在黔西北的威宁县,杨光早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知名人物,这位土生土长的农家孩子,从小就怀揣着与多数同龄人不一样的梦想,一名作家梦。为了这个梦,近20年来,他从中学,到大学,再到如今的三尺讲台,始终坚持不懈,笔耕不辍。也因为如此,他一度被人们戏称为“农民作家”、“农民诗人”、甚至是“文化流氓”的骂名。近日,恰逢杨光早的又一作品集《六角雪花》签约出版即将问世向全国发行,记者走进了这位人们眼中的“怪才”。
梦想:在“狼爱上羊”的故事中点燃
杨光早1977年出生在素有黔西北“四大梁山”称号之一的马摆大山脚下,也许是马摆大山那独特的高山大草原环境和马摆河落日的余辉,孕育出了这个从小就敢规划自己人生目标的年轻人,使他显得格外的爽朗、睿智、幽默而宁静。家乡的林子、田野、山歌、野猪棚,还有那勤劳善良的人群都是他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他文章里的感情、韵味、特色等等,一切都是来自这片山水的结晶。
谈起与文学结缘,杨光早的思绪又飞回到了当年的中学时代。那时,由于从小就听到老人们经常说起马摆大山的一些神奇传说,知道马摆原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威宁史上曾经的彝族土司乌撒的侄儿,后人将属于他们家领地的这座最高的一座大山按其名字来命名。
“那时候我就想,别人都能用名字来命名大山,我用什么方法来把我的名字也延续下去呢?”
上中学后,这个念头一直在他心中难以忘怀,渐渐的他明白了一点,作为农家孩子来说,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唯一的途径就是努力读书。除了其他科目外,他对语文课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一次学校组织的中学生作文竞赛上,他的作文在全校获得了三等奖。得到老师和学校的肯定后,小小的杨光早突然醒悟,这不就是自己从小追求的梦想吗?
1994年,杨光早考入毕节师范学校,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处女作《故乡那满坡满岭的荞麦》荣获全省中师生作文竞赛一等奖,同时,一些相应的稿件开始见诸报端,从此,他对写作的钟情更达到了极近偏执的程度。一有空,就四处寻找课外文学书籍,吮吸文学的乳汁,每有感触便写上一段,初尝写作喜悦的他如同歌词里狼爱上羊一样的疯狂爱上了写作。
激情:在痛并快乐中燃烧
“搞文学创作虽不能发财,甚至连养家糊口都可能有问题,但这是一种人生追求,一种磨练,更是一种生存态度,它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自身的素养。” 尽管一路走来充满辛酸和无奈,杨光早却丝毫没有后悔。说这话时,这位土生土长的汉子依然葆有浑然天成的率真和清新,一如他的作品,悄悄地在这块黑土地上破土而出,逐渐广为人知。
师范毕业后,他象众多毕业生一样回到家乡中学教书。他勤于钻研,教法新颖,语文课深受学生喜爱。生活和文学往往面临着失败的命运,但还要追寻诗意的快乐和梦境的收获。所以,与众多的教师不同的是他的勤奋。工作之余,他孜孜以求的读书,每年都要从自己为数不多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钱来订购了各种文学刊物,如饥似渴的阅读中,他更钟情于描写乡村生活的小说,一本本读着,一次次和自己身边的农民生活对照、比较。从中积累小说的叙事技巧,学习名家的语言风格,领会作品的深刻内涵,在观察思考生活的同时笔耕不辍,他的作家梦就这般于不知不觉中酝酿着。
几年间,他以当地农村生活为素材的小小说《打工归来》、《女人和狗》、《骚动的乡风》等作品陆续问世。得到了文学界一些作家的好评。先后受到省城,北京等地一些文学界邀请出来参加笔会,探讨创作经验。
每一次的成功,他的自信都会随之增加,那种喜悦,久久让人回味。喜悦之后,一切又将回归自然,由于家中农村的父母年龄越来越大,生活需要赡养,加之结婚后儿子的相继出生,生活的负担一天比一天重。往往每个月的工资还没有发下来,他就要琢磨一家人的生计,怎么开支等?梦又回到了现实。但无论生活怎么艰辛,他对文学的创作始终坚持不懈。劳苦之余,用文字来宣泄和寄托心中的忧愁,成了他精神生活的另一种寄托和追求,成了他做不完的梦!
2003年,他的小说《雪落无声》艰难诞生,那是一段以戏谑的眼光描写农村人的生活风貌,以清新浪漫的笔调和洞察入微的细腻描写,真实的反映了山里人的生态和心态的文章,弥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也因此,他在农民作家、农民诗人的头衔外,由于文中带“黄”,在痛并快乐中又多得了个“流氓作家”的称号。
执著: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我的父母用犁铧耕耘大山的土地,我用我的笔耕耘大山的土地,我的思想沿着父辈走过的路圆着自己的作家梦。” 杨光早说,能当一名教师是他的梦想,因为从大山里出生的他知道,上学是山区孩子们的梦想,如能用自己的梦想去点燃孩子们的梦想,到孩子们梦想成真之日,自己的梦想也真正成真了。为了这个梦想,杨光早在经过多方联络之后,于2008年元月在自己所在的麻乍中学校园里办起了文学杂志《荞苑》,一时间,爱好文学的师生们纷纷踊跃投稿,在全校师生里掀起了一股创作热。各种由师生们创作的诗歌、散文频频发表在杂志上,用当地一位知名作家的话说:文字粗糙有何妨,结构杂乱无大碍,只要稍作剪裁润色,就都是品位极高的素材。尤其是字里行间奔涌着的那来自乡村生活的真实情感,是任何人靠道听途说所不可能写出来的力作。而且最关键的是培养了乡村学生们的写作能力和自信心,那对于学生们来说,就是一本好书。
十余年来,杨光早对文学仍然痴心不改。其间他甚至放弃了一些走出乡村学校的机会,但他对那片养育他的大山已有了太深的爱。用他的话说,这片土地能激发他的灵感,任他的心灵之笔走马如飞,让他的灵魂悸动,也使之安宁,走过了花季雨季,错过了玫瑰花开,在他的明眸深处,仍然闪动着马摆大山那片迷人的原始风景。
2009年,杨光早的第一部文学作品集《阳光的心路历程》正式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而事隔一年之后,第二部作品集《六角雪花》也与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签约出版。
当记者问到他今后的创作打算时,他腼腆地笑了:“这是我一生的希望,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第三、第四,甚至更多的作品出版。将来,在大家的努力下,金秋的草海,定会“百花齐放”。黑颈鹤的故乡,就像一位超凡脱俗的诗人,用嘤嘤鸟语和琅琅书声,弹奏出神奇乌蒙的天籁之音。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一定会坚持,因为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附:
雪落无声 杨光早
一九九九年冬天,纷繁的雪花无声无息地撒向大地,覆盖了山川,装饰着原野,冲洗净污浊的乡村小道。
麻尿坡脚下的土墙房顶炊烟袅袅。只听木板门“咯吱”一声,钻出来一个头戴虎头帽身披破棉袄的老者,弯腰从石磨上捧起一团雪放在黑不溜秋的茶壶里,转身进了屋。
老者名叫朱史团,他的老伴在十年前的一场雪灾中滑下了山崖,扔下他和八岁的女儿朱麻翠独自到天堂逍遥戏耍去了。如今,女儿长成了人见人爱的大姑娘,到城市里打工去了。只有一头叫麻花的母牛和朱史团相依为命。
麻尿坡脚下的人们说,除了走亲串戚,朱史团几乎和麻花形影不离。干活的时候,朱史团把麻花牵到田边地角,给它割最鲜嫩的草。累了便打一个盘脚坐在地上,卷一袋旱烟,嘴里念叨着一些什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麻花说。麻花似乎听懂了什么,有时“妈,没妈”的叫唤几声,眼睛里有泪花在转。每当这时,朱史团总要用粗壮的手抚摸麻花的脸,麻花便温顺的低下头来。
过了一会儿,门又“咯吱”地开了,朱史团弯腰提着一只冒着白汽的水桶向牛圈走去。麻花喝完盐水,温顺地睡在未嚼完的苞谷草堆上。朱史团这才发现,麻花的肚子大了许多,奶头开始光滑,尾巴下尿尿的地方红得有些煽情。
麻花要下崽了!
朱史团想到这里,心里有些压抑不住的冲动。朱史团有个怪癖,一高兴就想整两盅苞谷洒。但喝酒总得有个伴,于是他想到了赵老汉。朱史团心里明白,麻花下崽,赵老汉家的公牛功不可没。
前些日子,麻花不知怎么了,总是叫个不停,放出圈去,便像疯了一样地乱跑。直到赵老汉家的公牛把前脚搭在麻花的背上,朱史团才明白过来。
“啪!”赵老汉不知从什么地方蹦出来,一捧打在公牛背上。公牛一惊,来不及收回武器就从麻花身上极不情愿地跳下来。
“你疯球掉了?我都不管你管了做么子?”朱史团说。
“一哈哈还要犁地,让它狗×的干好事还犁个铲铲?”赵老汉说,“要不然你开我50块钱!”
“日怪,我还没听说过牛做事人还要帮球它开钱的道理!”
“烧酒总应该请我喝一盅吧。”
在朱史团和赵老汉讨价还价的时候,公牛追着麻花跑到一个平整的地方,先用舌头舔舔麻花的头,再舔舔身上的毛,然后伸起前脚爬在了麻花背上……朱史团看着麻花陶醉的样子,看着公牛投入地工作,胯下竟有一股液体热乎乎粘乎乎地顺着大腿直往下流。
“要球得!你说哪天?”
“等你的麻花下崽再说,省得你说我吃你!”
但朱史团是无论如何也捱不到麻花下崽了,他现在就想喝酒,一刻也不能耽搁。于是他给麻花倒了一瓢饱满的苞谷,提着一壶酒,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朝赵老汉家走去。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赵老汉一副球迷日眼的熊样,居然有老牛吃嫩草的福份!
赵老汉的老婆马氏,整整小他一轮甲子,是麻尿坡脚下少有的美人。没有谁知道他为什么会嫁给赵老汉。让人们更意想不到的是,不是说龙生龙凤生凤吗?如此漂亮的女人怎么可能生下一个傻子!这也是令赵老汉伤透脑筋的问题。
据说,赵老汉和马氏结婚了两年,夫妻俩不分白天黑夜地耕耘,马氏的肚子就是不见动静。因为此事,两口子互相责怪,闹到了村长那里。村长说这种事咋个讲,哪个认球得你们哪个的家私有问题?
“我能证明不怪我儿子!”赵老汉他爹从人群中钻出来说。
“咋个证明?你又没……”村长欲言又止,毕竟赵老汉他爹年长许多。
“我在床下听过几回,每次都数到一百多下,比我年轻时很球,哪里来的问题?”
赵老汉他爹话音一落,在场的人都笑晕了过去。赵老汉牵着马氏灰溜溜地跑回家里,又试验了一回。
这回一试一个准,十个月后,马氏为赵老汉生下一个八斤重的男婴。赵老汉一高兴,就为他取名叫赵八斤,然而赵八斤从小就有点憨,一年级期末考试,语文3分数学4分,还是全班前十名!据说他们班只有9个学生。赵老汉逢人就夸:“八斤成级差到是差,还好不偏科!”读到小学二年级,赵八斤干脆回家来放牛。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在家的都娶了妻生了孩子。赵八斤二十七岁了,还没有个合适的对象。
朱史团像个雪人一样钻进赵老汉家时,赵八斤还窝在被窝里。
“八斤,起来吃饭了。”马氏冲屋里喊。
“不起就不起,你们不给我说媳妇我就是不起。”
“你起来看哈哈,你老丈人都来看你了,咋个还没说?”
“哪个?”
“你史团叔!”
朱史团干咳了两声,赵八斤才一骨碌翻下床,“史团叔,麻翠回来了?”
“就这一两天吧,赶紧吃好饭去跟我看着麻花,好像要下崽了,我和你爹摆哈龙门阵。”
“要得!”赵八斤狼吞虎咽地干了一碗荞麦疙瘩,到朱史团家看牛去了。
赵老汉叫马氏添了几个菜,和朱史团面对面坐下,一边咂叶子烟,一边喝苞谷酒,一边摆龙门阵。马氏坐在火塘边,不时用眼睛瞅瞅朱史团。朱史团便有些心猿意马,三下五除二就把赵老汉灌得不省人事,拖着马氏钻进了被窝。朱史团怎么也不敢相信,他积攒了10年的公余粮,一分钟都没有就交给了马氏!
不知是出于对马氏的感激还是对公牛的报恩,麻翠一回来,朱史团便把女儿许配给赵八斤,和赵老汉打成了亲家。日怪的是,如花似玉的朱麻翠并不反对嫁给一个憨包!
开春的时候,朱史团和赵老汉一商量,杀了一头猪,择个良辰吉日,就把事办好了。之后,朱史团有事没事隔三岔五就往赵老汉家跑,去的时候当然不忘带上一壶自家酿的苞谷酒。每次都把赵老汉灌个烂醉如泥。朱史团的殷勤引起了赵老汉的怀疑。于是朱史团再次来的时候,赵老汉便装酒醉。朱史团见时机成熟,便心急火燎的把马氏抱到床上。朱史团掏出家伙正要行凶,赵老汉提着荞麦棒站在面前。这事很快又闹到村长那里。村长和朱史团是叔伯弟兄,就对赵老汉说:“老赵啊,酒能乱性你又不是认不得?”
“村长,再乱也不能乱到我老婆肚皮上去球噻。”
“算了算了,酒醉的不算数!”
“酒醉的不算数?你说的哈,你记着。”赵老汉窝着一肚子鬼火回到家,喝下半斤苞谷酒,趁儿子赵八斤不在家,冲进房按住了朱麻翠。
“爹,你整什么?”朱麻翠说。
“整什么?干你!你爹驴日的干我媳妇,论理我该干你妈还掉,你妈死球掉了,我就干你!”
“爹,你放开我,恁个做要不得,八斤回来看见不好!”
“我管球不了那么多,哪个叫你爹……”赵老汉一边咆哮,一边撕开麻翠的上衣,两手紧紧攥着麻翠丰满的乳房,右脚蹬掉麻翠的裤子。这时只听“呯”的一声,赵老汉口鼻流血,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赵八斤提着荞麦棒满眼充血地站在朱麻翠的面前。
屋外又开始下雪了,这是新世纪的第一场雪,飘飘洒洒,无声无息。
一辆警车冒着雪花急驰而来,带走了赵八斤。
第二天,朱麻翠踏着雪痕翻过麻尿坡,到城里打工去了。
第三天,朱史团和马氏扒开一块雪地,匆匆掩埋了赵老汉。所有的一切,似乎没有发生过,像这雪,无声无息。
只有两行足迹,深深浅浅地印在那条通往他们两家的路上。
←乡村教师杨光早和他的作家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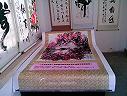
!["宇宙摇篮"会长李昌中出席钓鱼台大会[陈戈]](/UploadFiles/2013102033262043.jpg)
![“宇宙摇篮”会长李昌中简介(三)[记者:陈戈]](/UploadFiles/2013100370543505.jpg)